那么,现在就来到了8月27日,距离6月29日已经快三个月了。6月29日,我离开了学习、生活了五年的北京;8月27日,我在即将于此继续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三年或五年或更久的上海,写下这篇文章。
当然,我应该更早的写下此文,毕竟我于8月的15日就抵达了上海。但可惜的是,在宿舍断了两周的网、在天文台断了一周的网使得我只能将此文拖延到这个时候。不过,两周的误差在蜿蜒又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是那么的微不足道,因此也就随意了吧。
在北京生活的五年,谈不上多么的快乐,也说不上多么的不适,但总之也顺利的活过来了不是,也有了三五好友。如今到了上海,却与在北京认识的大多数朋友分别了。当然,要论分别,倒不如说一年前从师大毕业来得更,hmmm,炫烈一些。相熟的同学与朋友们,要么出了国,自此真的天各一方,连海上生明月也难以共此时;要么留在北京,继续在熟悉的城市中与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开始新的阶段;抑或是如我一般去到了其他城市,开始新的生活;又或是回到家乡,只为河两岸夜莺歌声飘绕。如此看来,6月的分别仿佛只是上一次分别的尾声,一场小小的余震罢了。
但无论如何,现在来到了上海。当然,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了,虽然前两次也只是走马观花一般,几乎不能算是来过,而现在我却要开始适应她,在其中活过下一个五年。初次面对这座宏伟的城市,我的确感到了一些无所适从,不禁怀念起北京,特别是海淀区的那种氛围来。当然,北京也是一座大都市。但与上海不同,海淀区总能给我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。在上海,每天骑车去台里的路上,路过一个个大型商场,面对远处新建的大厦,我总是产生一种幻觉:我真的在这里吗?或许这也是人面对新环境的某种保护机制吧。当然,我也不禁想到,那些出国的同学和朋友,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环境,心中又会作何感想,又将怎样去努力适应这样的环境呢?或许,我所面对的困难不及他们的分毫,可直到两周后的现在,我感到我仍然没有完全适应。不论适应还是不适应罢,生活总是要继续的。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逐渐麻木了我的神经,也渐渐使我感到“也就这样”。可当和朋友去其他地方恰饭的时候,总还是会有一些奇异的不适应感:我真的属于这里吗?
五年前,刚来到北京的我,是否也是这样的感受呢?当时,我花了多久才逐渐适应了在北京的生活呢?又是过了多久,才敢于离开习惯了的舒适的学校的小环境,一个人出去走走的呢?这些已然不记得了。当然,在这五年,乃至从我出生至今,纵然我记得很多事情,但也有更多事情是我远无法记住的。也许并不是全然忘记了,只是我以为我忘记了,但它们还等着某一天我触景生情,出来伏击我呢 笑)。在这样的新环境中,我也只能不断提醒我自己:“明天会更好,事情一定会好起来的”,来找回一点面对新事物的勇气。但我也清楚,如果自己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些新事物,所谓的“好起来”也不过是句空话而已。这样一个怪圈,还真是有意思。
好吧,东拉西扯了这么多,也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,也不知道与主题究竟有什么关系。那就稍微回归一下主题罢。上海,对我来说,的确是一个新的起点,一个新的开始。如果说在雁栖湖的一年是我在北京的尾声的话,那么现在,新的大幕,即将拉开。
最后,虽然不是很切题,也不是很切合环境,但还是冒昧引用一首诗吧。
世味年来薄似纱,谁令骑马客京华。
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
矮纸斜行闲做草,晴窗细乳戏分茶。
素衣莫起风尘叹,犹及清明可到家。
临安春雨初霁,陆游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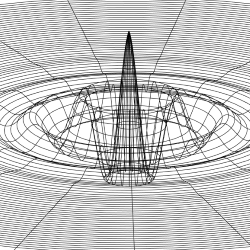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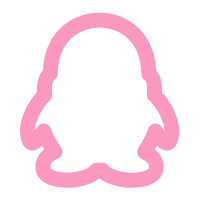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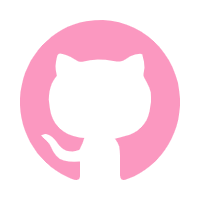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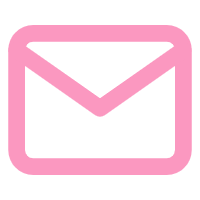

Comments NOTHING